君子生非异,善假于物也
Lianhe Zaobao carried a commentary by Professor Looi Chee Kit, Professor of Education at NIE and co-Director of the Centre for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in Learning, NTU as well as Dr Wong Lung Hsiang, Senior Education Research Scientist at the Centre of Research in Practice and Pedagogy, NIE. The writers noted that the advent of the AI chat programme ChatGPT sparked heated discussions in the education sector, and had been discussed in Parliament. The writers shared that teachers, students, and workers would need to embrace technology, as AI’s applications would only deepen. AI-generated tools were not the only means of cultivating AI literacy, but they had low barriers to use and could be used in almost all subjects. Wong highlighted the work of organisations such as AI Singapore, who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AI and AI literacy education in Singapore.

"信息素养和AI素养,是活在资讯时代的人当下或不久的将来必备的素养。简单来说,信息素养涉及获取及批判性地理解、整合信息的能力,和负责任地、有建设性地生产和发布信息的能力。AI素养事关了解及评价AI工具的功能、局限和造成的挑战,懂得负责任地善用AI来辅助决策、完成任务、提升生活品质等。"
人工智能(AI)聊天程序ChatGPT的问世,在教育界掀起热议,相关话题甚至登上国会殿堂。如果我们告诉你,ChatGPT——用户输入文字“要求”、系统生成文字“以文生文”的工具,不过是这一波可能冲击教育的AI工具的冰山一角,还有其他诸如“以文生图”——系统按用户的文字描述生成所要的图像或照片,以及“以文生视频”“以文生音频”“以文生电脑程序”“以图生文”等工具(统称为生成式AI),各类型的学生作业都能被AI“包下”,你会不会更不寒而栗?
其实,哪个颠覆性科技初登场时,不引起众声喧哗?10多年前互联网,尤其是搜索引擎开始普及时,也有人担心教师和课本的知识权威地位受到挑战。而今上网学习、整合信息已成为学校教学活动中经常性的学习任务,成为突破课时限制、培养自学能力和批判性思维等的利器。
ChatGPT之所以会一出场就屡遭教育界质疑,是因为它似乎在挑战源自农工业时代,至今仍被多数人认定为理所当然的教、学、评价方式。可人类早已进入资讯时代,整个教育理念应在培养“与科技共存、与科技成为战友”的师生和就业人士的大前提下“砍掉重练”。所以,相对其他相关评论文章聚焦于相对低层次(虽也不容忽视)的防作弊课题,或零散列举教学点子时,我们试图提升讨论层次——信息素养和AI素养,以及人—机“智慧伙伴”的理念。
信息素养和AI素养,是活在资讯时代的人当下或不久的将来必备的素养。简单来说,信息素养涉及获取及批判性地理解、整合信息的能力,和负责任地、有建设性地生产和发布(以网络、数码或传统印刷媒体的形式呈现的)信息的能力。AI素养事关了解及评价AI工具的功能、局限和造成的挑战,懂得负责任地善用AI来辅助决策、完成任务、提升生活品质等。
这些似乎都是技能,但为何华人世界却另行发明了“素养”一词(英文则借用了原指识字或读写能力的literacy)来概括呢?因为素养还包含对有关事物的概念理解,和相关的道德及社会价值观(上文提到的“负责任地”)等。
在本地,鉴于互联网已融入生活的方方面面,信息素养早成为显学。政府发布数码与信息素养框架,融入中学课程;国家图书馆也常年举办活动,提升公众意识。其中因假信息、网络诈骗频仍,事实核查成了信息素养的核心技能之一。另一方面,很多人或许还没意识到,在迈向智慧国2025的道路上,我们的生活正逐渐被更多AI设施或工具所围绕;孩子们长大后踏入社会,职场上的AI应用只会进一步深化。因而,以推动人工智能发展为宗旨的新加坡人工智能核心(AI Singapore),也持续推行AI素养教育。
ChatGPT可培养学生相关素养
ChatGPT一亮相,就有学者提出可利用它(或其他生成式AI工具)来培养学生的信息素养和AI素养。AI生成工具不是培养这两种素养的唯一手段,但它们胜在使用门槛低、使用体验饶富趣味、几乎所有科目都合用;更因为它们貌似智慧无边、才华横溢,却其实有局限、缺陷,正可利用。
如有人提出,教师可指示学生要求ChatGPT生成一篇与教学内容相关的短文,然后学生必须上网搜索文中所有论点的出处,并找出、纠正文中的错误信息或偏颇的观念,对内容和行文作出点评;个别学生还可以针对文中提出他们不同意的观点,与之展开一来一往的辩论。这些活动如一石二鸟,既能深化学习课程内容,又可提升信息素养,让学生未来对网络假信息更有敏感度。
这些AI生成工具,目前能生成的“作品”,对于教师或学习进度较高的学生来说,往往只是“初稿”等级,须好好修一修——除了可能得纠错,还得重新组织内容、增删具体论点和加入实例等。但就因为AI先起个头,至少初步筛选了作品素材,师生都不必从零开始“作文”,省下更多时间来组织思路,再以初稿为基础进行修改,把自己的思路表达得更精确,或边修文边改进思路。条件是学生在开始如此使用ChatGPT前,得先学好这从零开始的“技术活儿”;否则在开始使用后,也难把它的初稿修好。这就是人机分工,组成智慧伙伴的例子——善用人工智能来增强(而非取代)人的智慧。
拙文《拥抱机遇,应对挑战?——ChatGPT3的教育应用》(1月24日《联合早报·言论》)里探讨的“21世纪的学习者,懂得问对问题比对答如流更重要”的论点,与信息素养和AI素养都相关。
此“问题”可指输入搜索引擎的关键词组、向ChatGPT请教时的“问法”,或对任何能操纵的AI工具所下的指令。问对的、高素质的、符合语境的问题、设定最有利的条件,才能得到真正相关、高素质的答案或“作品”,或是AI工具符合预期及高效的操作成果。
一个常被提及的教学设计,是指示学生针对一个大主题,自拟问题请教ChatGPT,然后全班分享、对比各自取得的答案,以达致对学科知识的深度学习。若要进一步用以提升信息素养和AI素养,我们建议一个延伸活动:让大家挑选最相关、最有深度的答案,倒推、反思其问法“好在哪儿?”
打个比方,在战场上,某将领如果不懂得问对问题以精确评估战情,不懂得调兵遣将,不懂得变通,纵有百万雄师也搞不好会全军覆没。“智慧伙伴”理念的意涵,如同让机器当智囊、探子、尖兵,而人就身兼情报解读者和做决策(注意:尽信智囊(机器)不如无智囊)的将领。
信息素养还涉及负责任地制作及传播信息──不作假、不偏颇之外,还要考虑发布后对社会或当事人的可能负面冲击。生成式AI工具可能会生成“不负责任”的信息,如“从文到视频”的工具可生成深伪视频。因而教师可针对这些AI工具产出的具潜在问题的信息,请学生讨论:“如果把它放上网,会造成什么后果?”同样的,AI素养也包含使用及开发(若学生掌握相关技能)人工智能工具的道德议题,同样可采用类似的反思活动,让AI素养的培养更为全方位。
当然,我们理解一些人对ChatGPT的担忧──教育科技学者说了几十年“让电脑承担低层次、重复性的工作及记忆海量信息,留给师生更多时间思考和执行高层次的教学任务”,可ChatGPT等AI生成工具的功能,如同一夜间从“低层次”进阶到“中层次”,进一步“侵蚀”了一些本来仍该学的技能,把学生该驾驭的技能又推高了一层。这是否会导致另类数码鸿沟——信息/AI素养鸿沟呢?
例如,ChatGPT生成的文字可能不如高学习进度的学生自己写的作业,因而着手修改而学、思得更深入;但中、低学习进度的学生,可能自忖写不出ChatGPT等级的文字,反而有了偷懒的诱因?或许,针对ChatGPT教育应用要探讨的下一个课题,是差异教学的考量,例如为中、低学习进度学生另行设计针对性的AI辅助学习策略。这可另外为文探讨。
(作者黄龙翔是南洋理工大学国立教育学院高级教育研究科学家吕赐杰是学院教授)
Read the original article on Lianhe Zaobao.
Source: Lianhe Zaobao © SPH Media Limited. Permission required for reproduct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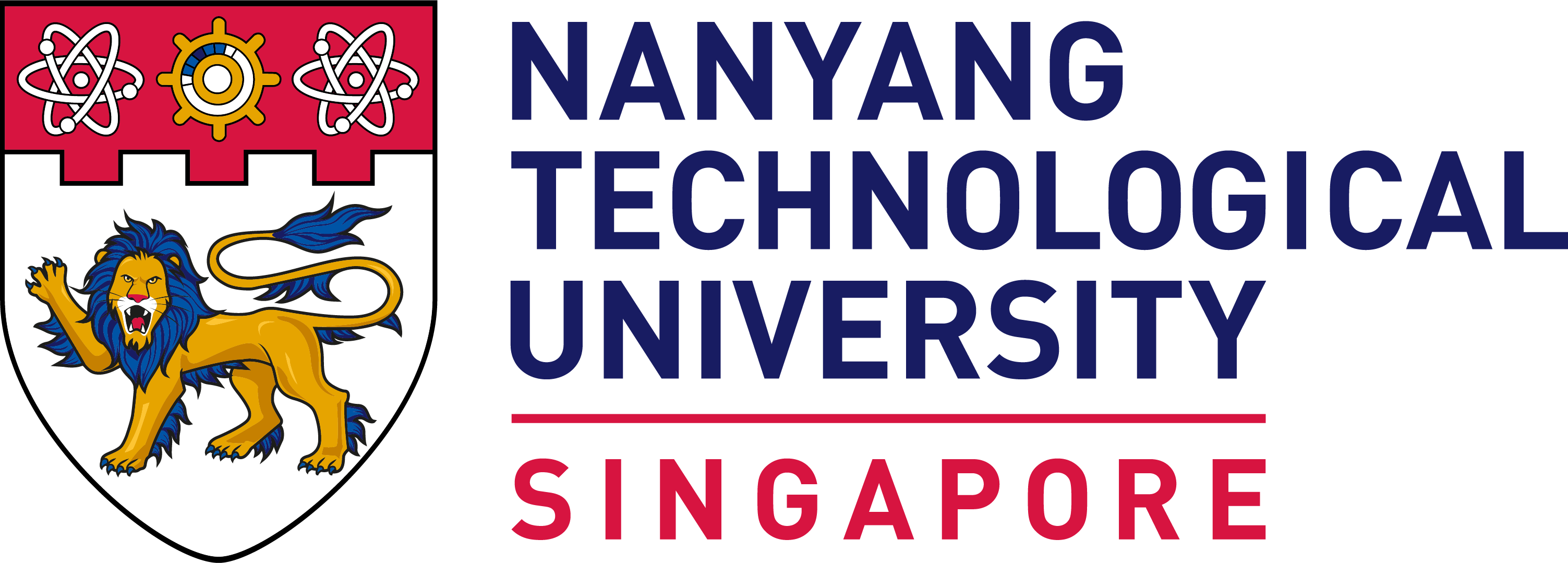




.tmb-listing.jpg?Culture=en&sfvrsn=f130c079_1)